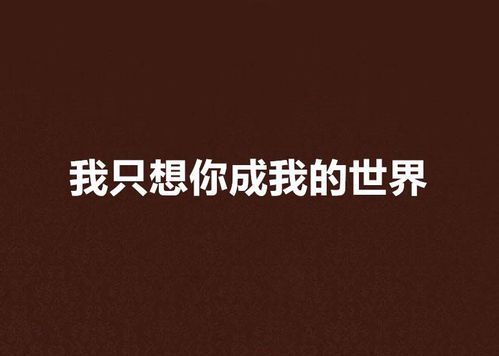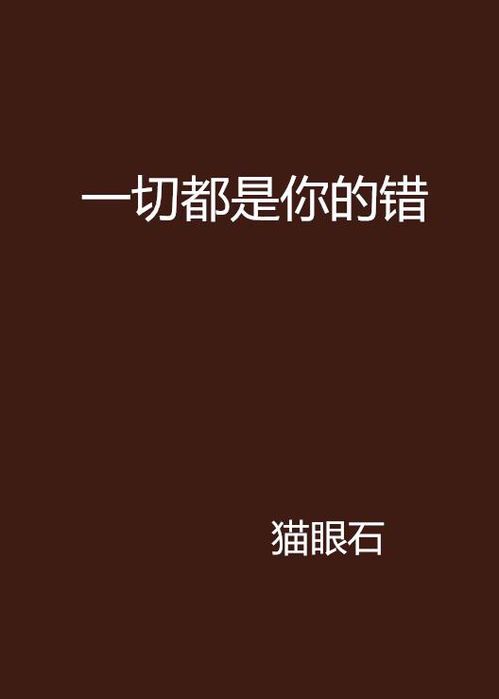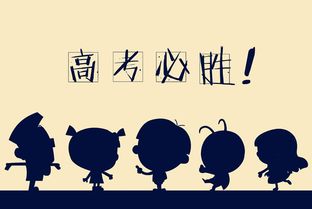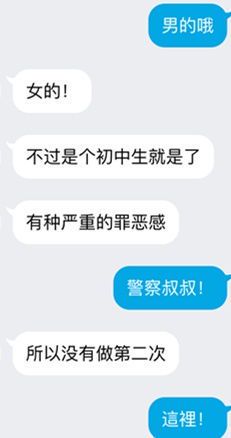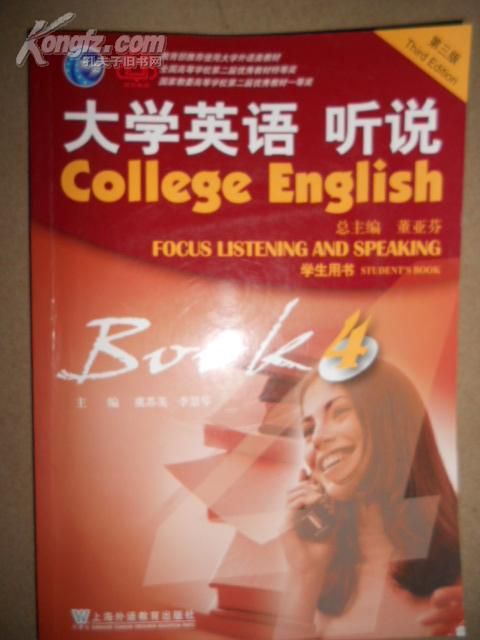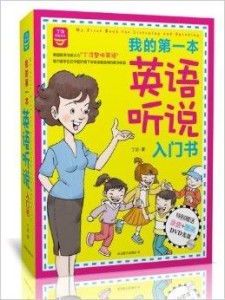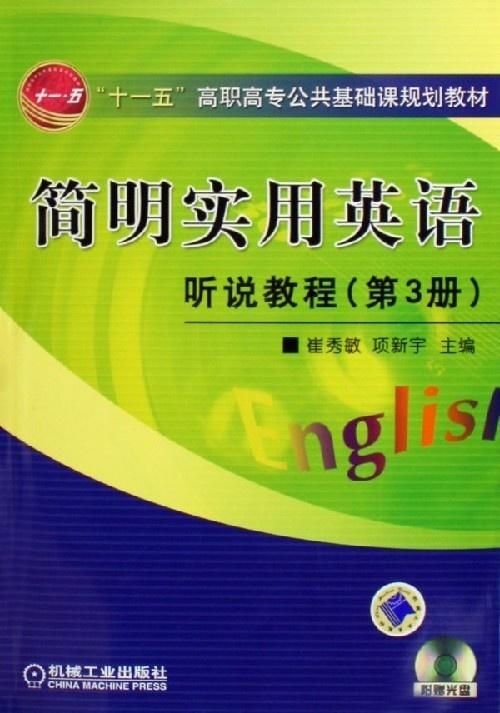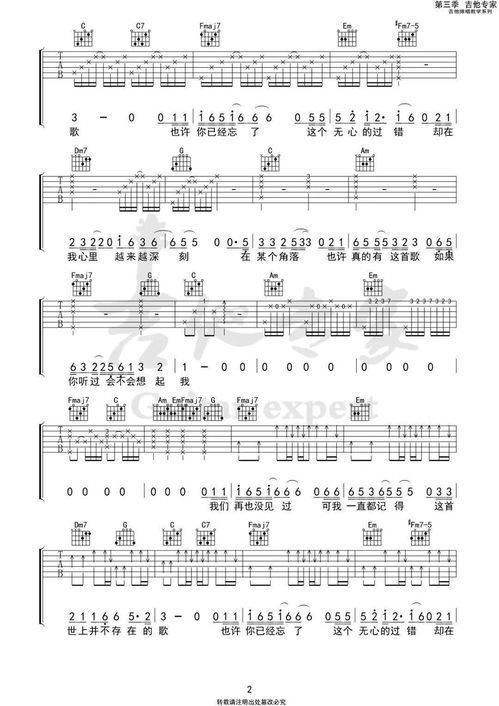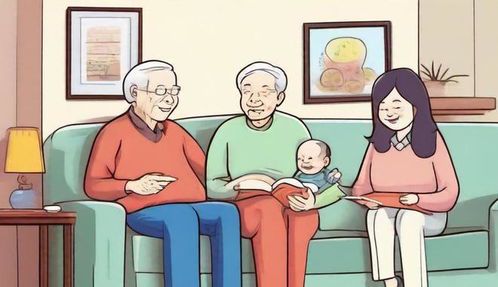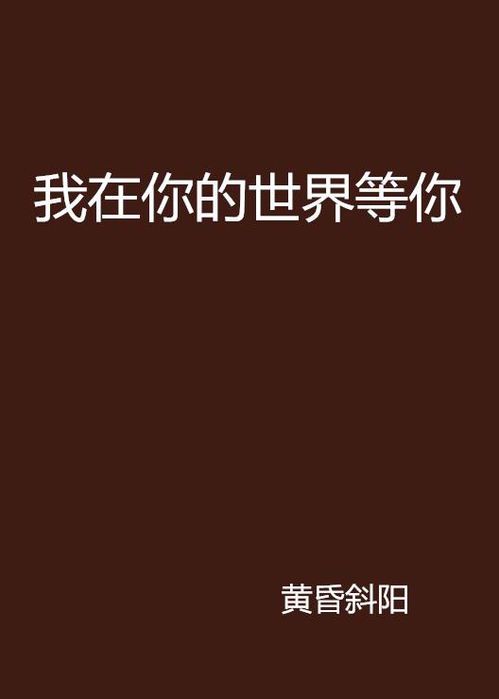在无数个平行宇宙的假设里,我们总被定义为独立的个体。可当某个黄昏的光线穿透你睫毛的间隙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你的世界正以分子渗透的形式重构着我的认知。那些你随手分享的咖啡渍形状,你抱怨过的地铁站名,甚至你惯用的那个错别字,都成了我大脑皮层上新生的沟回。
人类学中有个古老命题:当我们用同一双眼睛看风景,是否就在共享同一种人生?你教会我辨认天琴座的流星雨轨迹,而我的备忘录里至今留着你说"冬季大三角比夏天更明亮"时,呵出的白气在路灯下消散的弧度。这种认知的殖民如此温柔,以至于我开始用你的口吻给绿植浇水,对着你推荐的电影台词会心一笑。
语言学家说亲密关系会催化语法融合。我们发明了只有彼此能解的密码:把加班称作"给资本家上坟",用"菠萝事件"代指所有尴尬回忆。当你的四川方言混进我的东北腔调,某种新的混合语正在诞生。就像那些被对方养刁的味蕾——曾经厌恶的折耳根,如今成了深夜食堂的暗号。
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凌晨三点。当我下意识用你的思维方式解决工作难题,当我的购物车出现你钟爱的那个小众香氛品牌。这种精神层面的镜像反应,比任何物理距离的靠近都更具侵略性。柏拉图说的"被劈开的圆形人"或许是个骗局,我们分明是在相互涂抹的过程中,诞生了第三种存在形态。
量子纠缠理论在宏观世界的拙劣印证,大概就是某天我突然停下脚步——银杏叶坠落的速率,云层分裂的角度,所有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自动关联着你存在过的证据。你的世界不再是你,我的眼睛也不再纯粹属于我。这种缓慢的献祭仪式里,我们交出了部分自我,换来了更辽阔的边疆。